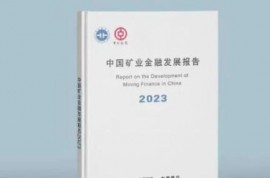橫潭的地理位置十分優(yōu)越,明朝弘治二年,平定譚觀福之亂后,朝廷設(shè)從化縣治于此,弘治七年,遷往馬場田。橫潭復(fù)歸番禺管轄。新建花都區(qū)時,從番禺劃歸花都區(qū)。橫潭位于廣花平原上,距今花都區(qū)新華鎮(zhèn)僅一公里,物產(chǎn)豐富,土地肥沃,適合農(nóng)耕。據(jù)民國《花縣志》卷六《實業(yè)志·耕地狀況》記載“第三區(qū)按民國時,橫潭在花都區(qū)第三區(qū)除在西南之黃歧山、小朱村、馬步坳一帶較多水災(zāi)外,其他則水災(zāi)均少。
土質(zhì)松厚,為全縣之最佳者”,耕作條件十分優(yōu)越。又“第三區(qū)則種稻外,以種麥與馬蹄為多,蠶桑亦漸有經(jīng)營,而荔枝則全縣以本區(qū)三華店、畢村為盛。”據(jù)有人研究,追至明末,橫潭就有“姓龍荔枝基”姓袁荔枝基”等多處荔枝基。'可見,至少在明末,橫潭已經(jīng)出現(xiàn)基塘種養(yǎng)的經(jīng)營方式,而且數(shù)量已經(jīng)非常可觀。
除了農(nóng)業(yè)之外,橫潭附近的礦產(chǎn)資源也十分豐富,位于橫潭墟東部三里左右的青石、海灰石礦“其石青色,可制白灰,以供建筑及肥料之用,現(xiàn)有灰窯數(shù)間,銷流傳甚廣,邑中農(nóng)田多賴之。”雖然這里說的是民國時期的情形,但也反映出橫潭附近的礦產(chǎn)資源分布狀況。橫潭的交通條件十分便利,經(jīng)濟繁榮。水運方面,花都區(qū)境內(nèi)的水運可通舟楫而達于省會者,主要有橫潭水和白泥水。
而橫潭水“東自蘇炯而出遷大東涉、仙閣邊至嶺頭接龍口而下,由九曲、青石轉(zhuǎn)西而會于橫潭。西自正逞而出,經(jīng)鐵山,瀝貝、小涉而至龍口與蘇恫水合,又出自牛枯屯發(fā)源。出數(shù)里東接正城之水,東流而下山貝葉村。自此稍東則與青石并歸橫潭,惟橫潭可通舟楫以達省會。”從橫潭經(jīng)大益埠、五和墟入巴江河出入廣州,可以通行載重在一萬斤的木船,并且有客貨船來往于兩地,在當(dāng)時是一個熱鬧的航運碼頭。
陸路上也更加接近廣州,還是橫潭墟和獅嶺巡檢司的所在地。橫潭墟建于明弘治二年從化縣城設(shè)址橫潭時興建,舊址原為村中一條直街,故城“橫潭街”。建縣后隨著經(jīng)濟的發(fā)展,商店日益增多,原來的墟市已經(jīng)不能容納,遂由附近的鄉(xiāng)組織“經(jīng)緯堂”,集資在村北從化縣城舊址擴建新墟。加上當(dāng)時橫潭有渡船直通廣州的便利條件,商業(yè)日趨繁盛,墟內(nèi)陸續(xù)建有商店多間,成為花都區(qū)中南部重要的集市。有人研究,橫潭村由于昔日設(shè)立從化縣城和巡檢司的緣故,形成了以橫潭大街為中心的煙民藩庶,商賈輻揍,集市繁榮的景象。
從更加長遠的角度來講,花都區(qū)后來的發(fā)展趨勢表明,橫潭所處的位置,也是后來花都區(qū)經(jīng)濟中心所在的區(qū)域。不僅如此橫潭村還有著昔日從化縣治的良好基礎(chǔ)。明代弘治二年平定譚觀福之亂后,在此設(shè)立從化縣治,后于弘治七年遷往馬場田。橫潭重歸番禺管轄。花都區(qū)建縣時,從番禺劃歸花都區(qū)。明代對橫潭村曾有過一番修建,有商業(yè)大街、城墻、衙署、書院等等設(shè)施,已具縣城規(guī)模。
據(jù)民國《花縣志》記載“從化城址從化縣城在橫潭墟,今屬獅嶺巡檢分治,其城隍廟、儒學(xué)地屋,及故城基址猶存”也就是說,直到民國時期,昔日的從化縣城城址,依然有所保留。換言之,清初建縣之時,如果在此基礎(chǔ)上加以修葺,大可不必舉行浩大的工程,省去大筆經(jīng)費。“工程浩大,需費浩繁,非數(shù)萬余金,鮮可濟事。”的難題,也許可以迎刃而解了。
可以說,在橫潭設(shè)立縣城,兼?zhèn)淞私煌ū憷?jīng)濟基礎(chǔ)雄厚,還可以利用原有的建筑,節(jié)省大批建設(shè)費用的有利條件,這些優(yōu)勢無論是黃士龍《建縣條議》的正遷還是后來的平嶺,都無法匹敵的,橫潭理應(yīng)是最為理想的縣治選擇。花縣縣治沒有選在橫潭,似乎頗讓人有些費解。但是事實上,橫潭村的確沒有被當(dāng)局所看好。
盡管在康熙二十六年的《花縣志》中沒有提及在花縣縣治的選擇的時候,橫潭村沒有作為對象的原因。但是修撰于雍正年間的《從化縣新志》云“楊五都橫潭村屬廣州府,后五年十八山寇姚觀祖復(fù)嘯聚巖谷間,命行軍布政陶魯、兵備僉事袁慶祥殲其眾,事定,建議曰縣治密邇郡城,而據(jù)賊巢甚遠。不能控馭。今流溪馬場田地方,土沃民醇,去廣州二百里,宜函徙以圖久安。”不難看出,從化縣治遷徙的原因是“縣治密邇郡城,而距賊巢甚遠。不能控馭”。
同樣出于控馭全縣的需要,當(dāng)事人普遍的意見認為,花山設(shè)縣,主要的目的在于防備花都區(qū)北部的花山地區(qū)的匪患,而橫潭離花山比較遠。“雖然在山丘起伏的地方選擇城址毫無疑問不如在平坦的地方好,但人們有時也利用顯目山丘和懸崖來增強城墻的防御功能。”所以,花都區(qū)建縣時,就沒有考慮地理位置相對優(yōu)越,經(jīng)濟繁榮的橫潭村。
由此也可以看出,統(tǒng)治者的最高目的是在尋求地方的安寧,而不是求地方的發(fā)展,在安寧的前提下能取得發(fā)展固然很好,若兩者發(fā)生矛盾的,則寧舍后者而取前者。正遷,位于花縣城今花都區(qū)花城鎮(zhèn)北三里,這里地勢險要,屬于花山地區(qū),向來是盜賊出沒之處。廣東巡撫李士禎曾說“花山地方延裹,其間的各有車頭塾、曹尚、沙帽嶺、屋源水、正逞、錘村、沙規(guī)、三扶田、黃竹湖、落塘鋪等處,率皆萬山重疊,路徑險僻,自古及今,積賊難除”,是當(dāng)時花山盜聚集的巢穴之一。
據(jù)黃士龍稱,正遷一帶地方“群峰插天,林木深阻,回環(huán)相度”地勢險要,向來為兵家必爭之地。李士禎在剿滅花山盜時,曾“會同番禺、清遠、從化三縣官兵,駐扎于正遷、屋檐水、三塊田、落塘埔、鐘村、沙蛆等處,酌量形勢,各安兵一二百名,以千、把統(tǒng)之,俱相機堵剿”日。如果在此設(shè)縣,地近花山,便于彈壓。這是正遷作為縣治的主要優(yōu)勢,也是黃士龍想在正遷建立縣治的原因之一。
另外,正通居于清遠、番禺、南海等縣中部,交通便利。黃士龍設(shè)想中的花都區(qū),應(yīng)當(dāng)是以正遷為縣治,另由番禺、清遠、從化三縣會同委官勘查,凡是界連山炯,都圖地堡鄉(xiāng)村,人民的田土稅畝應(yīng)割歸新縣管轄,這樣的話,大約可以劃得周圍三百余里地方,徑直一百余里,可得錢糧五六千,建立一個中等規(guī)模的新縣。然后,可以設(shè)置官員,廣集民眾,開荒辟土,同時建設(shè)縣署、官衙、倉庫學(xué)宮、神廟、市肆、民居等等。而且建筑縣城的材料,石料、磚石、木料等項,可以就近取用而用之不竭。
至于人夫等事宜,因為附近人民飽受匪患襲擾,而建縣是一勞永逸,有力地方的事情,因此,人民一定樂意聽從差遣,而無不踴躍。再加上如果是從南、番、清、從等縣劃撥人口的話,估計單單成丁就應(yīng)該在、萬左右,修筑規(guī)模僅僅數(shù)十丈的小城,工程量,也不過是每百人出一丁,百日可以建成,每丁也僅僅提供一天的勞役而已,不會給人民造成多大的困難,而致民怨沸騰的。關(guān)于建筑費用,則可以采取地方捐券,不必動用公款。
建縣治于正遷,在黃士龍等人的設(shè)想中,也就是一個周回三百里,人丁五六萬的中等規(guī)模的縣。地域包括了原來南海、番禺、從化、清遠等縣的環(huán)花山一帶的地區(qū),也即是以花山為中心地帶的縣域。從這個角度來說,正遷不失為一個較為理想的選擇。黃士龍爭逞設(shè)縣的理想最終破滅了。新縣的縣城沒有選在正遷,而是確定在平嶺。黃士龍對此是頗有微詞的。后來在修撰《花縣志》時,黃士龍也多次提到自己的征遷建縣的方案。“
康熙十二年,有征剿之役,番禺邑侯王公之麟拉以偕行,軍于正遷,仰見群峰插天,林木深阻,回環(huán)相度,唯有設(shè)邑建城,可握喉吭。王侯稱善,復(fù)虞力役繁興,遂不果。”黃士龍的建縣于正逞得想法是由來已久,早在康熙十二年,與番禺縣令王之麟征剿花山盜,駐扎于正逗時,就已經(jīng)有在此建縣的想法。只是由于王之麟擔(dān)心力役繁興,導(dǎo)致人民不滿,而只得作罷。黃士龍不甘心自己的理想就此破滅,在向廣東巡撫李士禎呈上的《建縣條議》中,他又重申自己在正遷建縣的理想。但是,從后來建縣于平嶺,可以知道,他的夢想并沒有實現(xiàn)。
正如后來花都區(qū)建縣時縣境的劃分一樣,正遷也沒有按照他的構(gòu)想成為縣治。因為最后清廷批準(zhǔn)花都區(qū)建縣時,由于三水、清遠、從化等縣,以“該縣地方原屬小邑,錢糧無多,且去花山新縣意遠,人丁稅畝,應(yīng)請免撥”為由,拒絕劃撥人丁、錢糧,規(guī)定花都區(qū)只能具備小縣規(guī)模,而不是中等縣規(guī)模的縣治。另外,依據(jù)中國傳統(tǒng)的風(fēng)水學(xué)理論,正遷營四望皆平,也不是城址的最佳選擇。
隨著后來花縣縣治選在平嶺之后,正遷營的地位也隨之下降。僅有“城守營兵八名防汛,今改為塘鋪”。平嶺作為縣治,主要的原因是平嶺地理位置接近花山,位于花山南麓。建縣前,是平嶺營所在。據(jù)民國《花縣志》卷四《兵防》記載“康熙二十一年內(nèi),巡撫李士禎會同總督吳大發(fā)官兵,分四路并進,剿撫兼用,始底蕩平。因調(diào)右翼鎮(zhèn)游擊一、守備一、千總二、把總四、兵八百八十名,分駐平嶺、高浦、石林、麻岡等處防守”。
設(shè)立縣治,駐兵防守,便于彈壓,維護地方治安。而且,城東十里有蘇炯水,從山后流出,城西五里有正遷水,牛枯屯水,向南匯流與橫潭水合。縣西南三十五里為橫潭水,源出縣南正遷諸溪,西南流獅嶺,水陸交通,也較為方便。另外,選擇平嶺作為城址,主要是風(fēng)水的關(guān)系,也即堪輿家的作用也不可忽視。中國古代城市的選址,往往與傳統(tǒng)的風(fēng)水觀念緊密相關(guān)。平嶺是李士禎與各縣知縣,以及堪輿家共同選定的。
家的意見所得出的結(jié)論。風(fēng)水學(xué)上認為,“地貌條件,山來時有彎轉(zhuǎn),有環(huán)抱,又與平原交接的”結(jié)穴”處為首選。風(fēng)水認為是山環(huán)之地,“吐唇”之地。此類,地高不旱,居下而不被沖刷。”以此而論,平嶺正好是花山“連亙串珠,轉(zhuǎn)亥入首”之處,又處于與廣花平原交接的地方,而且,三面環(huán)山,左輔唐帽嶺,右擁石巖塘,恢曠而南,正對白云高峰。地勢北高南低,利于通風(fēng)、采光。與風(fēng)水學(xué)的選址原則,幾乎完全吻合,實為風(fēng)水學(xué)的首選。
平嶺地區(qū)地理位置靠近花山,駐兵防守,便于彈壓。基本處于新建花都區(qū)的中心地帶,交通便利,便于管理。同時具備風(fēng)水學(xué)的優(yōu)先原則,再加上地勢較為平坦,建筑城池時,又可以就近開采器料。因此,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會選擇在平嶺建城,而舍棄了橫潭和正遷。縣城的城址選擇確定之后,即著手籌劃營建。但花都區(qū)新建,原無基礎(chǔ),工程又相當(dāng)浩大。
據(jù)廣東巡撫李士禎、兩廣總督吳興柞的奏疏稱“新設(shè)花都區(qū),城垣、廟宇、衙舍、喚匠,估計材料、石磚、灰瓦價值,匠夫工食,嚴加核減,尚計需銀五萬九千七百一十九兩,折合銀圓為八萬二千九百四十三元。”當(dāng)時呈請于藩司內(nèi)褲先借銀二萬兩給發(fā)興工,完工后補還。后于康熙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吏部奉旨批復(fù),傷令勸輸鼓勵修造,不許動用公款。因而采用黃士龍原來所提的建城意見,分攤給百姓負擔(dān)和勞役。其辦法如下
砌筑城墻垛口所需的青磚,按各司成丁指十六歲以上的男丁,每人負擔(dān)青磚四十塊。各司約計成丁五六萬,共得青磚二百三四十萬塊。青磚清磚招匠就地?zé)欤牰∶褡孕匈I辦。每丁出銀三分多。貧者可割草砍柴交給磚窯,折價換磚。至所需木料,全部就近山林砍伐。將縣城附近的荒山、荒地及城內(nèi)可以建宅的空地,按地價招人承購,所得款項撥作基建之用。
全部工程所需人力,由每一成丁服勞役一天,并以“是役也,為各司謀安堵,其勞當(dāng)各司共之”為理由,指定番禺的獅嶺、慕德里、鹿步三司,南海的三江、金利二司、從化的流溪司、清遠的滔江、回歧二司,三水的青江司所屬居民,都同樣要參加勞役。縣城的整個規(guī)模是周四百四十丈,高一丈四尺,厚一丈二尺,上廣尺,下廣尺。
辟四門,上建樓槽,環(huán)以月城,警鋪一十二間,錐諜六百三十個,成交內(nèi)外各開馬路,廣一丈,有泄水濱,處議用磚石包砌,東西北三面皆山,南無壕塹。惟廣聚商民以資稠密業(yè)經(jīng)估計達……部埃工筑竣日,請辟四門額名,撰記勒石永垂。規(guī)制實為省城北門鎖鑰,城四門及雄蝶用青磚,城基用白石,城墻用泥磚建筑。中國古代城市的布局規(guī)劃有著鮮明的特點,即遵循中心布局的原則。
中心布局原則是中國城市不論是首都或者地方城市,在規(guī)劃時都要首先選擇中心,中心位置確定后,再向四周擴展,框定城市的總體范圍。花縣城的建設(shè)就是這樣的。在縣城選擇之后,即開始籌建縣城。首先選擇縣城的中心,中心位置的選擇,是根據(jù)地理條件、需要和可能確定的,而不是任意選擇的。中心位置選擇適當(dāng)與否,會直接影響到城市的總體規(guī)劃。在縣城的中心布置縣級朝廷所在的衙署。
縣署在城中西南,其制中為大堂,左為贊政廳,右為龍亭,庫中進為穿廊,為后堂,左為耳房,庫右為架閣,庫又中進為知縣衙,門樓一座,正廳一座,燕室一座,書齋、廚舍,群房各其四周繚以臂垣。由大堂前為露臺,下為房屋,中為信道,按原缺石廳在焉。兩翼為六房及承發(fā)鋪長卷廟。廟后為吏舍,信道前為儀門,左為土神祠,前為迎賓館,右為禁獄,又前為大門,上為憔樓,翼以榜神,東為族善廳。西為申明廳,正南為照墻,橫街東西各建一坊,以拱衛(wèi)縣宇,臨民出治云。
典史衙在縣署左,門樓一座,正廳一座,燕室一座,書房、廚舍各具”縣衙作為一種主要的政Z機構(gòu),對一個縣級行政單位有著重大的意義。因為“清朝衙門在清朝社會里一直是一種最令人注意的機構(gòu),因為衙門是極其重視行政管理的文明古國的主要政Z管理工具。在清朝朝廷各級的無數(shù)司署中,縣級衙門對當(dāng)?shù)厝嗣裆钣绊懽畲螅驗榭h級衙門是他們最直接、最經(jīng)常碰到的皇權(quán)形式。
縣衙門也是地方朝廷與非正式的地方權(quán)力代表協(xié)商的主要中心。這種私下的活動與公開事務(wù)一樣,是縣級衙門的一種重要職能。總之,縣級衙門既為朝廷權(quán)威的重要工具,又為政Z交流的主要場所。由于衙門職能的多樣性和重要性,它是一個極其繁忙的機關(guān)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”,'也就是說,在一個縣級政區(qū)中,縣衙最主要的功能是代表中央朝廷直接管理地方,教化人民。同時也是官方與地方權(quán)力代表、民間的交流場所。這些特征決定了它是一個極其繁忙的機關(guān),是縣城以及一個縣級政區(qū)的政Z、文化中心。
縣衙作為一種主要的政Z機構(gòu),他的主要職能是通過知縣以及他的下級官員來執(zhí)行的。自知縣以下的多級衙門官員均在衙門內(nèi)工作和生活。衙門官員在任職期間,一般住在衙門內(nèi),很少外出。知縣的主要責(zé)任是維持社會安寧和征稅。知縣作為主要行政官員,他的公務(wù)主要是掌管縣衙門、調(diào)節(jié)賦稅和力役、審理訴訟、助老人、的職責(zé),祭祀、教化人民、提高文化水平和控制民間風(fēng)俗。此外,他還負責(zé)扶支持士子,甚至監(jiān)督他們的學(xué)業(yè)。朝廷委托給縣級行政機關(guān)幾乎都由知縣一人承擔(dān)。
因此,知縣的事務(wù)十分繁忙,例如花都區(qū)的首任知縣王永明自上任以來,開山湮谷,修筑城垣等事,每事事必躬親,任勞任怨,親自撫慰流離各處的村民還鄉(xiāng)歸農(nóng),遍于窮谷宣上諭。以致“積勞成疾,遵赴玉樓”,病死在任上。知縣工作的勞累、繁瑣可見一斑。甚至就連清朝最高統(tǒng)治者雍正皇帝也不得不承認“州縣事務(wù)實為繁多”而議添設(shè)州縣副員一人,以理衙署以外事務(wù)。花縣城在平嶺營址,后靠群山,前臨平原,左輔唐帽嶺,右擁石巖塘,恢曠而南,正對白云高峰,形勢雄壯。
因為平嶺地方東西北三面環(huán)山,僅南面是平原,止可建三里之城。屬于小縣的規(guī)模。中國封建社會中,城墻與城市有著非常密切關(guān)系。“對中國人的城市觀念來說,城墻一直極為重要,以致城市和城墻的傳統(tǒng)用詞是合一的,城這個漢字既代表城市,又代表城垣。在帝制時代,中國絕大部分城市人口集中在有城墻的城市中,無城墻的城市中心至少在某種意義上不算正統(tǒng)的城市。”的花縣城的城墻“周四百四十丈,高一丈四尺,厚一丈二尺,上廣尺,下廣尺按原缺··…處議用磚石包砌。”是十分堅固的。
城墻上開辟四門,上建樓稽,環(huán)以月城,警鋪一十二間,雄諜六百三十個,規(guī)制實為省城北門鎖鑰,形成了以城墻為主的完備的防御工事,起著防盜御寇,保護城市的作用。但是在城墻的南面沒有建壕塹,主要是為了廣聚商民以資稠密。可以說花縣城的規(guī)劃,除了考慮防御的作用外,還著眼于以后的經(jīng)濟發(fā)展。在城郊內(nèi)外各開馬路,廣一丈,有泄水濱。馬路為石砌,首任知縣王永明“鑿石填坑而成坦道”是花縣城的主干道。縣城內(nèi)的主要建筑物的布局嚴格有序,主次分明,井井有條。
縣署為政Z中心,占據(jù)全城的主要位置。花都區(qū)的縣署與典史衙,位于全城的中部地區(qū)。縣署以入前述,需要說明的是,縣署還附帶一些重要的設(shè)施,如土神祠,在縣署儀門內(nèi)左,“舊制以為懲創(chuàng)之所。每時節(jié)朔望,縣官行香。”醫(yī)學(xué),在縣治。陰陽學(xué),在縣治東。預(yù)備倉,在縣治東,官廳一座,傲三間,曬場地一段,共周七丈等。
花縣城的壇廟建筑主要集中在縣城的東面,主要有保佑全城安全的城陛廟,在縣城東門旁,“廟中無專祭,惟縣官上任先日齋宿,啟祀于神”,所冀風(fēng)雨以時,年歲豐穩(wěn),民物咸遂,四境皆安社翟壇,在縣城西面,城外半里,以祈求一年風(fēng)調(diào)雨順,五谷豐登。康熙二十六年《花縣志》卷一建置中稱花縣城“南無壕塹,惟廣聚商民以資稠密”。據(jù)此,縣城的商業(yè)中心應(yīng)在南面。
花都區(qū)學(xué)宮、義學(xué)位于縣署的東部,形成花都區(qū)獨特的文化區(qū),這里南對城墻,背靠縣衙,交通便利,地理環(huán)境十分優(yōu)越,是花縣城的標(biāo)志性建筑。花都區(qū)學(xué)宮,在縣署東,“坐子向午,前為權(quán)星門,門前砌石,方廣一十八丈,對為照墻,東建興賢坊,西建育才坊,兩旁立下馬石,門中為神道,渴者入由東出。
西門內(nèi)石為伴池,跨以石橋,東為更衣亭,西為按原缺,進為廟門,立戟二十四,內(nèi)東為宰牲亭為什么廚,西為神庫,中為雨道,翼以兩旁,半為丹埠,西為神位,高為露臺,環(huán)以石欄,上為先師廟,由東慶出。廟后為明倫堂,前為廣屏,翼以四齋學(xué)舍。后為敬一亭,后為尊經(jīng)閣,由東齋南左折而出為禮門,循東慶直南出為儒學(xué)門。”其規(guī)模較為壯觀。學(xué)宮是國家承認的正統(tǒng)文化中心,是地方社會對民眾傳播教化的標(biāo)志性建筑,也是朝廷對人民思想控制、灌輸封建倫理思想的主要機構(gòu)。
只有取得功名或者有志于仕途的人才能在學(xué)宮里學(xué)習(xí)生活。正如國外漢學(xué)家所說的城陛是以自然力和硅為基礎(chǔ)的信仰中心,因而可以說是用來控制農(nóng)民的神學(xué)宮是崇拜賢人和官方道德榜樣的中心,是官僚等級的英靈的中心,學(xué)宮還是崇拜文化的中心。這在康熙二十六年的《花縣志》卷二學(xué)校記中也有體現(xiàn)“賢侯姐豆其政而忠信倡之,學(xué)宮姐豆其教而忠信導(dǎo)之,弟子姐豆而忠信體之,執(zhí)其器,端其容,敦其本,將見昔之習(xí)于頑梗肯化而為詩書之子”。
義學(xué)在縣署東北,“知縣王王永明延聘本學(xué)凜善生員譚鼎輝,設(shè)教訓(xùn)迪,每年捐送修儀二十四兩。凡有志士子無力延師者,令其就學(xué)肄業(yè)。”'就是說,義學(xué)是為有志于考取功名,而無力聘請私塾教師的士子們開辦的。此外,除建設(shè)縣治以外,花都區(qū)境內(nèi)還設(shè)有獅嶺巡檢司署和水西巡檢司署。花縣建縣前,廣東巡撫李士禎在蕩平“花山盜”之后,于“番禺慕德里之平嶺設(shè)營防守,調(diào)右翼鎮(zhèn)游擊一員,千總二員,把總四員,目兵八百八十名,中屯太營余分防要害。”
花都區(qū)建縣后,官府認為,應(yīng)在花都區(qū)境內(nèi)設(shè)立兩個巡檢司,遂于橫潭、水西兩處設(shè)立巡檢司。設(shè)有“花都區(qū)駐防城守守備一員,千總一員,把總二員,目兵四百名。”'的“獅嶺巡檢司署在縣境西南橫潭街,原隸番禺縣,明初洪武三年建,今割隸花都區(qū)署,仍舊制。水西巡檢司署,在縣東北,近水西鄉(xiāng)。基地半屬從化,半屬清遠,盜賊由之出沒。明崇禎間,議立清從州,不果。后設(shè)番、清、從守備府,今廢。今立花都區(qū),議設(shè)巡檢司于此,以扼險要,署埃創(chuàng)建。”兩個巡檢司的設(shè)置,主要是為了便于防備花山一帶的賊寇,鎮(zhèn)壓人民的反抗,還有屏障廣州的職能。